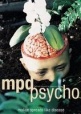房东蒋先生
| 片名: | 房东蒋先生 |
|---|---|
| 其它片名: | /Last House Standing |
| 导演: | 梁子, 干超 |
| 摄影: | 梁子 |
| 片长: | 56分钟 |
| 年份: | 2002年 |
| 类型: | 纪录片 |
| 国别: | 中国 |
| 语言: | 国语 上海话 |
| 格式: | dv |
| 制作机构: |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|
影片概述 . . . . . .
再过一个月,老宅就要被拆掉了.它曾经一次次地醒来,对他说再见;是他对它说再见的时候了,是永别的时候了。他,房子的主人,蒋先生,不住地说:他恨透了这幢拴住他一生的房子。
来自北京的女记者贸然闯进了老宅,她发现这里弥漫着她不能渗透的谜。她试图去解开蒋先生和老宅的秘密,却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场奇怪的多幕剧中。她沮丧地发现自己只是个孤独的局外人。令她感到悲哀甚至绝望的是,历史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很多东西。它使这些关于老宅的秘密越来越沉重,沉重地让蒋先生缄默而迷恋。
老宅见证了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十里洋场,记住了上海解放的历史关头,铭刻下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,注视着改革巨变的新上海。老宅因此不再是没有生命的器物,它将历史变革、家族盛衰、人情冷暖、梦境现实一古脑地交给蒋先生,去忍受,去承担。这一次轮回,是整整六十年。
女记者隐约感受到困扰蒋先生的精神漩涡源自老宅。他没有结过婚,那是因为他厌恶家庭;他没有太多的朋友,那是因为他信仰怀疑;他戒不了吃西餐、喝红茶、打英文信件的习惯,那是因为他依恋着旧时生活。可是,一切的一切,和老宅又有什么关系呢?这一次,她的勇往直前在一位上海老人的心灵深处搁浅了。窗前的那棵白玉兰就要开花了,阳光斜照着蒋先生孤单的身影。屋外,打桩机在嚣叫,高耸入云的新建筑俯瞅着都市中心的这一片废墟;屋内,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,蒋先生独守着老洋房最后的日子。
六十年的坚守最终还是崩溃。拆迁前夜,蒋先生又唱又跳......
来自北京的女记者贸然闯进了老宅,她发现这里弥漫着她不能渗透的谜。她试图去解开蒋先生和老宅的秘密,却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场奇怪的多幕剧中。她沮丧地发现自己只是个孤独的局外人。令她感到悲哀甚至绝望的是,历史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很多东西。它使这些关于老宅的秘密越来越沉重,沉重地让蒋先生缄默而迷恋。
老宅见证了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十里洋场,记住了上海解放的历史关头,铭刻下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,注视着改革巨变的新上海。老宅因此不再是没有生命的器物,它将历史变革、家族盛衰、人情冷暖、梦境现实一古脑地交给蒋先生,去忍受,去承担。这一次轮回,是整整六十年。
女记者隐约感受到困扰蒋先生的精神漩涡源自老宅。他没有结过婚,那是因为他厌恶家庭;他没有太多的朋友,那是因为他信仰怀疑;他戒不了吃西餐、喝红茶、打英文信件的习惯,那是因为他依恋着旧时生活。可是,一切的一切,和老宅又有什么关系呢?这一次,她的勇往直前在一位上海老人的心灵深处搁浅了。窗前的那棵白玉兰就要开花了,阳光斜照着蒋先生孤单的身影。屋外,打桩机在嚣叫,高耸入云的新建筑俯瞅着都市中心的这一片废墟;屋内,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,蒋先生独守着老洋房最后的日子。
六十年的坚守最终还是崩溃。拆迁前夜,蒋先生又唱又跳......
导演阐述 . . . . . .
在个性的舒展中呈现-梁子访谈录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5年01月10日17:13 东方全纪录
片名:《房东蒋先生》 (2002年DV纪录片作品)
片长:56分
摄像:梁子(使用机型 SONY PD100AP)
编导:干超(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)、梁子(女)
类型:人文类纪录片
梗概:再过一个月,老宅就要被拆掉了。梁子租住老宅,真切地感受着房东——一位典型的上海“老克勒”蒋先生与这幢老洋房之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那种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关系。老宅见证了三十年代上海的浮华,解放后的变迁,文革时期的狂暴,以及今日社会的巨变。片中两个年龄、性别相异的人物,萍水相逢,在语言、性格、生活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的冲撞中,展现了人性中最为细腻、独特、温情、无奈的一面。
梁子
从搜索得来的各样文章中,碎片式的介绍组合着一个梁子的印象——生于北京,军人的后代,自己也当过兵。作为一名女摄影师,出入过中越战场,深入过青海、西藏高原,三次只身前往非洲,后又去了阿富汗。先后出版了《一本打开的日记》、《独闯非洲高山王国——一位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纪实》、《西非丛林的家——我与塞拉里昂迪曼人》等纪实书作。目前,她的第四本有关东非红海岸边纪实的书作也即将完成。同时,梁子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合作完成了电视纪录片《非洲并不太远》(四集)、《跳吧,波尔卡》、《房东蒋先生》等。其中,2002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《房东蒋先生》入闱上海第十届国际电影电视节,并荣获“2003中国·横店影视城杯全国纪录片大奖人文类大奖(金奖)和2004韩国EBS国际纪录片节大奖 ,同时该片被第49届爱尔兰科克电影节特选。
从非洲的丛林到上海的老城,独特而个性张扬的北京年轻女性与细腻而怪谲的上海“老克勒”之间的碰撞,在梁子的DV中是怎样呈现的呢?
房东蒋先生
受访者:梁子(女) 摄影师 纪录片自由创作者
访问者:刘洁 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
时 间:2004年8月10日 晚上
地 点:北京明星街一茶社
刘洁与梁子
独特思绪与生命同在
刘 我来的路上一直在琢磨,该怎么称呼你。摄影师?纪录片编导?DV人?独立制片人?作家?旅行家?……你最愿意别人称呼你什么?
梁 自由摄影师。
刘 但如果我从纪录片这个角度来说,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更合适呢?
梁 随便,我也不知道,无所谓。“DV人”不适合,因为我现在用DV拍摄不是特别多,而是把它作为副业。“独立制片人”也不适合,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独立制片人!那天朱羽君老师说我就是,可我不独立,我哪儿独立了,我还要靠别人呢!只能算半个纪录片编导吧。现在有点乱,有的人说我是作家,我说谁作家呀,天天坐在家里吧,我觉得特恶心,因为一说我是个作家,我就觉得特恶心,丢不起那个人。
刘 那我们沿用自由撰稿人的叫法,就叫你纪录片自由创作者,可以吧。
梁 也可以,但是我一般对外都是自称自由摄影师。
刘 我第一次看到你,是偶然在凤凰卫视的一档像公益广告那样的节目里,你正在讲你如何前往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一个叫塔巴姆的小山村,如何与非洲人相处,如何“拿下”那个诬陷你的女保镖……当时只觉得你真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后来,我又在纪录片《房东蒋先生》里又看到你,个性是那么张扬,但就是因为这种个性的尽情舒展,使得整部片子透射着一种光彩。我不得不用一个俗语——“你真牛”,来表达我的敬意。
梁 我这辈子特别顺。想当兵,16岁就到陕西当了兵,想放电影就放了电影,想学摄影就学了摄影,想去青海就去了,想上老山前线就去了,想去西藏也去成了,去完非洲、阿富汗,我还打算去伊朗呢……我是想到就干,就敢干。人家说“三思而后行”,我说“三思”完蛋,是“而不能行”。
刘 但是,可以考虑稍微周全一些嘛。
梁 没用。很简单,到非洲最担心、最担心的事不就是被强奸吗?被抢劫都没这个担心,还有爱滋病吧。退一步讲,强奸不怕,反正结过婚了,怀孕做掉!而爱滋病,我咨询过了,就是300只蚊子叮了爱滋病人同时再叮你,才会得。但是,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强奸,什么地方没强奸,是白天来、是晚上来、是前面来、后面来、左面来、右面来……想那么多更害怕,想得多就更有压力。
刘 有人说,你是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去,是这样的吗?
梁 才不是的,怎么会呢!这绝对是一种美妙的玩法,至少比“游园”带劲多了,我觉得我这么做,很值!很有意思!但那些地方不宜久留。不管怎么说,还是都市多样化的生活好,咱们习惯这里的一切,当然,再好也不能总赖在这不动吧。
刘 《房东蒋先生》是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吗?
梁 应该算第二个。第一部是我第二次去非洲,在塞拉里昂拍的,那是逮着什么拍什么的,在上海电视台跟干超一起攒了4集21分钟的片子。
刘 那是你在拍照片的时候同时拍的吗?
梁 当时,第一次在非洲南部的小山村,特寂寞,没事干,时间大把。就觉得要是带个摄像机就好了。因为摄影是固定的,摄像机是可移动的,好多东西光用摄影图片其实表现力是不够的。如果能拍摄到一些移动的、行走的画面,就会更精彩,更完美。当时想带,但怕抢劫,再者人们也说,搞摄影的就别搞摄像了,搞了摄像就搞不了摄影了,两个别搅和,于是我想那就执着搞摄影吧。
刘 后来又觉得摄像是很有必要了?
梁 一到那里,时间一大把,有时爱滋病人快死了,说话的过程呀,根本纪录不了,如果有摄像纪录就会特别精彩,爱滋病人身上的皮肤一拽,是那样的,可照片只能看到那皮肤松松垮垮的样子,没什么意思。所以,第二次去的时候,我就想着买了一个数码摄像机。
刘 什么型号的?
梁 索尼PD100 AP。2002年我打算到西非塞拉里昂,临走前,没钱,找了一家公司买了一台,我借了出来,可这离我出发去非洲只有5天了,但我没用过,我就给中央电视台一哥们打电话,可他是编导,也不是搞摄像的,怎么办,来不及了,因为我还要办签证、打电话联系什么的,他说这么办吧,推拉摇移停4秒。
刘 呵呵,你就记住了这个?
梁 我就琢磨,摄像和摄影关键的不同就在于它有推拉摇移,它要移动,摄影是静止的。所以我就不停的推—拉—摇—移—,中间就嗒嗒嗒嗒停4秒,但镜头老是晃荡。当时也没演练,到了塞拉里昂以后,才看着说明书进行演练,哆哆嗦嗦地抖,拉吧是噔噔噔噔的,是一节一节的,不是“刷”地特平稳,总是拉一点,犹豫,再拉一点,呵呵,老头儿这个片子(《房东蒋先生》)里,也有这种情况,停了很长时间了还再拉一点。
刘 老头儿的这个片子是用索尼PD150P拍的吗?
梁 也是这个机器,PD100AP。那时还没买150呐,我是这次出发去东部非洲小国厄立特里亚的时候才买的。这次片子明显好得多,因为在拍老头时学了不少招术。
刘 你到阿富汗是在拍了《房东蒋先生》之后?
梁 是在干超编的时候去的,是在这个过程中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5年01月10日17:13 东方全纪录
片名:《房东蒋先生》 (2002年DV纪录片作品)
片长:56分
摄像:梁子(使用机型 SONY PD100AP)
编导:干超(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)、梁子(女)
类型:人文类纪录片
梗概:再过一个月,老宅就要被拆掉了。梁子租住老宅,真切地感受着房东——一位典型的上海“老克勒”蒋先生与这幢老洋房之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那种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关系。老宅见证了三十年代上海的浮华,解放后的变迁,文革时期的狂暴,以及今日社会的巨变。片中两个年龄、性别相异的人物,萍水相逢,在语言、性格、生活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的冲撞中,展现了人性中最为细腻、独特、温情、无奈的一面。
梁子
从搜索得来的各样文章中,碎片式的介绍组合着一个梁子的印象——生于北京,军人的后代,自己也当过兵。作为一名女摄影师,出入过中越战场,深入过青海、西藏高原,三次只身前往非洲,后又去了阿富汗。先后出版了《一本打开的日记》、《独闯非洲高山王国——一位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纪实》、《西非丛林的家——我与塞拉里昂迪曼人》等纪实书作。目前,她的第四本有关东非红海岸边纪实的书作也即将完成。同时,梁子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合作完成了电视纪录片《非洲并不太远》(四集)、《跳吧,波尔卡》、《房东蒋先生》等。其中,2002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《房东蒋先生》入闱上海第十届国际电影电视节,并荣获“2003中国·横店影视城杯全国纪录片大奖人文类大奖(金奖)和2004韩国EBS国际纪录片节大奖 ,同时该片被第49届爱尔兰科克电影节特选。
从非洲的丛林到上海的老城,独特而个性张扬的北京年轻女性与细腻而怪谲的上海“老克勒”之间的碰撞,在梁子的DV中是怎样呈现的呢?
房东蒋先生
受访者:梁子(女) 摄影师 纪录片自由创作者
访问者:刘洁 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
时 间:2004年8月10日 晚上
地 点:北京明星街一茶社
刘洁与梁子
独特思绪与生命同在
刘 我来的路上一直在琢磨,该怎么称呼你。摄影师?纪录片编导?DV人?独立制片人?作家?旅行家?……你最愿意别人称呼你什么?
梁 自由摄影师。
刘 但如果我从纪录片这个角度来说,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更合适呢?
梁 随便,我也不知道,无所谓。“DV人”不适合,因为我现在用DV拍摄不是特别多,而是把它作为副业。“独立制片人”也不适合,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独立制片人!那天朱羽君老师说我就是,可我不独立,我哪儿独立了,我还要靠别人呢!只能算半个纪录片编导吧。现在有点乱,有的人说我是作家,我说谁作家呀,天天坐在家里吧,我觉得特恶心,因为一说我是个作家,我就觉得特恶心,丢不起那个人。
刘 那我们沿用自由撰稿人的叫法,就叫你纪录片自由创作者,可以吧。
梁 也可以,但是我一般对外都是自称自由摄影师。
刘 我第一次看到你,是偶然在凤凰卫视的一档像公益广告那样的节目里,你正在讲你如何前往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一个叫塔巴姆的小山村,如何与非洲人相处,如何“拿下”那个诬陷你的女保镖……当时只觉得你真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后来,我又在纪录片《房东蒋先生》里又看到你,个性是那么张扬,但就是因为这种个性的尽情舒展,使得整部片子透射着一种光彩。我不得不用一个俗语——“你真牛”,来表达我的敬意。
梁 我这辈子特别顺。想当兵,16岁就到陕西当了兵,想放电影就放了电影,想学摄影就学了摄影,想去青海就去了,想上老山前线就去了,想去西藏也去成了,去完非洲、阿富汗,我还打算去伊朗呢……我是想到就干,就敢干。人家说“三思而后行”,我说“三思”完蛋,是“而不能行”。
刘 但是,可以考虑稍微周全一些嘛。
梁 没用。很简单,到非洲最担心、最担心的事不就是被强奸吗?被抢劫都没这个担心,还有爱滋病吧。退一步讲,强奸不怕,反正结过婚了,怀孕做掉!而爱滋病,我咨询过了,就是300只蚊子叮了爱滋病人同时再叮你,才会得。但是,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强奸,什么地方没强奸,是白天来、是晚上来、是前面来、后面来、左面来、右面来……想那么多更害怕,想得多就更有压力。
刘 有人说,你是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去,是这样的吗?
梁 才不是的,怎么会呢!这绝对是一种美妙的玩法,至少比“游园”带劲多了,我觉得我这么做,很值!很有意思!但那些地方不宜久留。不管怎么说,还是都市多样化的生活好,咱们习惯这里的一切,当然,再好也不能总赖在这不动吧。
刘 《房东蒋先生》是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吗?
梁 应该算第二个。第一部是我第二次去非洲,在塞拉里昂拍的,那是逮着什么拍什么的,在上海电视台跟干超一起攒了4集21分钟的片子。
刘 那是你在拍照片的时候同时拍的吗?
梁 当时,第一次在非洲南部的小山村,特寂寞,没事干,时间大把。就觉得要是带个摄像机就好了。因为摄影是固定的,摄像机是可移动的,好多东西光用摄影图片其实表现力是不够的。如果能拍摄到一些移动的、行走的画面,就会更精彩,更完美。当时想带,但怕抢劫,再者人们也说,搞摄影的就别搞摄像了,搞了摄像就搞不了摄影了,两个别搅和,于是我想那就执着搞摄影吧。
刘 后来又觉得摄像是很有必要了?
梁 一到那里,时间一大把,有时爱滋病人快死了,说话的过程呀,根本纪录不了,如果有摄像纪录就会特别精彩,爱滋病人身上的皮肤一拽,是那样的,可照片只能看到那皮肤松松垮垮的样子,没什么意思。所以,第二次去的时候,我就想着买了一个数码摄像机。
刘 什么型号的?
梁 索尼PD100 AP。2002年我打算到西非塞拉里昂,临走前,没钱,找了一家公司买了一台,我借了出来,可这离我出发去非洲只有5天了,但我没用过,我就给中央电视台一哥们打电话,可他是编导,也不是搞摄像的,怎么办,来不及了,因为我还要办签证、打电话联系什么的,他说这么办吧,推拉摇移停4秒。
刘 呵呵,你就记住了这个?
梁 我就琢磨,摄像和摄影关键的不同就在于它有推拉摇移,它要移动,摄影是静止的。所以我就不停的推—拉—摇—移—,中间就嗒嗒嗒嗒停4秒,但镜头老是晃荡。当时也没演练,到了塞拉里昂以后,才看着说明书进行演练,哆哆嗦嗦地抖,拉吧是噔噔噔噔的,是一节一节的,不是“刷”地特平稳,总是拉一点,犹豫,再拉一点,呵呵,老头儿这个片子(《房东蒋先生》)里,也有这种情况,停了很长时间了还再拉一点。
刘 老头儿的这个片子是用索尼PD150P拍的吗?
梁 也是这个机器,PD100AP。那时还没买150呐,我是这次出发去东部非洲小国厄立特里亚的时候才买的。这次片子明显好得多,因为在拍老头时学了不少招术。
刘 你到阿富汗是在拍了《房东蒋先生》之后?
梁 是在干超编的时候去的,是在这个过程中。
获得奖项 . . . . . .
2004年韩国EBS国际纪录片节大奖
2004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“横店杯”纪录片评选大奖(金奖)
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年度纪录片评选二等奖
2006年第二届卡塔尔半岛国际电视节国际纪录片铜
2004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“横店杯”纪录片评选大奖(金奖)
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年度纪录片评选二等奖
2006年第二届卡塔尔半岛国际电视节国际纪录片铜
评论列表(0) . . . . . . ( 发表新评论 ) ( 更多评论 )
幕后花絮 . . . . . . (上传花絮) (展开所有)
个体状态的平等进入
刘 说来也巧,我的上一个访谈,是在大连做的,所谈的内容也是涉及到“老宅”的拆迁,那个片子纪录了老宅里拆迁户的群体印象,而《房东蒋先生》纪录的是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心里感受。你是先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,还是租住了这个房子之后才发现了他?
梁 2002年夏末,因为我要跟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,剪我的那部去塞拉里昂拍的片子。住酒店的话,费用太大,有个朋友就说找个地方给我住。他说他认识一个老头儿,老头儿有17间房子,三层楼,就他一个人,没结婚,也没工作过,到时给他些钱,他家离电视台大概走十分钟就到。只是老头儿有点怪,希望我跟老头儿处好一点,别跟他闹意见。当时我也没多想,他有17间房子,这么大,怎么住我也不会打搅他呀。
刘 后来呢?
梁 我到上海后,带着行李跟朋友就去了。去之前,我们跟老头儿打了电话,到了老头儿家外面,看到周围正在拆迁,朋友说老头儿出来迎接你了,我当时一看,呀!老头儿穿着特白的衬衣,雪白雪白的,灰色的西装,烫得特别平整,头发弄得一丝不乱,油头粉面的,这么精神个老头儿!这么讲究的老头儿!心想家里一定特干净、特好,那些房子也满满当当的像客房一样的。我挺高兴跟他上去了。开了门,破铁门咣咣的,一层什么东西都没有,空的,二层,只有几个破椅子,到了三层一看,整个一个垃圾场,因为他要搬迁嘛,东西全用一些小纸盒子装着,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破破烂烂的,有几件小家具,破床、破电视机,在那还树着个梯子什么的,他家墙上还被凿了个大洞,外面还传来很大的冲击钻的声音,“得哑——”的,特吵、特乱。
刘 那你没有立即走掉?
梁 我一进去,朋友就跟我道歉说,梁子对不起,我不知到这里要拆迁,咱们不住了,重新找个地方,又没床什么的,怎么住呀。但我一想,老头儿反差这么大,这房子上来的时候,是摇摇晃晃的感觉,再回头一看老头儿,那么西装革履的,那么笔挺的,简直跟这个房子格格不入!其实,这时我根本没想到会拍什么,我就是有一种好奇,我就说,不走了,我不走了!老头儿其实也不是特想让我住,说没床什么的,我说铺个垫子,地铺也可以。老头儿特别不情愿地找了个垫子。当时,屋里面特乱,全是土,特乱、特脏。等我晚上从电视台回来,灯光很黑暗,放着周璇的歌,老头儿已经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,一个带扶手的简易沙发上铺着白毛巾。一想我这是在大上海,一想不远处就能看到的锦江饭店,我看着那白毛巾,就特来气,我特别忌妒地说,你把它打扫了干什么!你换成白毛巾干什么!老头一看我特厉害,说客人来了总要打扫干净的呀!然后,我们也没什么话说,我也根本没想到要拍什么片子。
刘 当时没想到,但是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想要拍他的?
梁 很快。第二天,我去电视台跟他们说了这个怪老头儿,反差大,老房子里总有30年代的感觉,可房子又要拆迁,他已经是个“钉子户“了。我也直觉到,单从这些,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东西,但究竟有什么,还不知道,同时也在犹豫,是单纯拍照片,还是拍片子,我还没想好。电视台的人听了以后就说:“赶快拍片子呀!”我当即决定拍片子了。
刘 你当时带着你的PD100AP?
梁 我当时是带了这个机器来上海的,要没带也不会拍了。
个性张扬的自然纪录
刘 从介绍你的文章中来看,你一直关注的是城市之外的人和事,这次怎么把关注点落在了最具城市特色的上海,落在了最具上海人特色的蒋先生身上?看来,你关注的兴趣点不仅仅是以地域来划分的,那么,这个兴趣点是由什么来确定的?在什么情景下,你萌发了要纪录房东蒋先生的念头?
梁 我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只觉得他挺怪的,反差太大,特别想了解他,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,当然我之所以能拍成他,也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,也是挺好奇的,而且我这人是个见面自来熟,才去一两天很快我们就搞得特熟。但实际上我特痛苦,我根本就不愿进他家,因为他家靠近锦江饭店,锦江饭店是个五星级的,特豪华,上海电视台也是高楼大厦,里面条件特别好,是全国一流的。可我来到上海,窝在这么一个地方,心里特不痛快。
刘 当时没想到去跟电视台借个机器,请人来跟你拍?
梁 没想。我当时想的就是,即使拍,也不能打搅老头儿太多的生活,我能感觉到老头儿是个非常安静的人,我本人也刚住进那里,而我和电视台的人也不熟,又是第一次合作。我没接触过老头儿这样的人,老头也没接触过我这样的人,他爱安静,我本身又躁得慌,如果我再带人来拍,乱乱哄哄,这绝对不现实。老头不喜欢的人,他都不让进门。最后,我都跟他特熟了,曾经带过两个人来,他很勉强,不屑一顾,他很傲。
刘 你一开始就想清楚怎么拍了吗?
梁 没有,没想,不太明确。拍老头,是顺手拍的。那时我一早就到上海电视台去跟干超他们一起剪我那部非洲的片子,我就会跟他们说,昨天拍的什么什么,人家就问怎么拍的,我就说怎么怎么拍的,人家就说要这样、要那样。我老是恶心老头儿,讲老头儿的笑话,什么呀一个破牙膏皮还擀了又擀的,他们说这个情节太好了,应该拍,一个摄像也不停地说怎么怎么拍。另外,他们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,说梁子你一定要抓住这个题材,因为这样的事、这样的人特少,很难得。
刘 在拍《房东蒋先生》时,脑子里有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,什么叫纪录片,纪录片应该怎么拍?
梁 没有,我现在都没有。你现在要让我说什么是纪录片,纪录片该怎么拍,我也不知道。
刘 那在你的直觉中,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的?
梁 我只觉得纪录片,就是纪实性要强,是真实的,当然我觉得手法是最重要的,如果中国有10样,世界上就应该有50样,而且还有其他超过50样的,你还可再搞定51样,也无所谓。但它一定是真实的、不是去摆的、不是虚构的,仅此而已,就够了,只要这个事是真实的,完整不完整,有没有前因后果,都没关系,但只要它是真实的就可以了。至于手法,是不是纪录片的手法,还是什么什么手法,都可以,访谈也是纪实手法,它也是一个手法,一个方式。
刘 关于真实问题我们在这不讨论,顺你这个意思,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按照一些固定的框框去拍纪录片,那你怎么会自觉意识到这一点?
梁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,因为摄影。因为我在摄影上已经走过了那种必须按规定性、规则性的东西去拍的过程,一想我就觉得特别恶心,但我想跳却很难跳出来。所以,我拍纪录片的时候,就再不想这样做了,再不要手把手去学,再不希望从什么书去学了,我不想知道什么规则,因为你知道有了规则,要打破它就太难了,与其你要打破它,还不如不想知道它。当然,最基本的拍摄是有规则的,比如推拉摇移,我过去不知道,现在我知道了,还可以停,还可以怎么怎么的,所以知道一点就够了,剩下的构图、用光等就是摄影的手段了。
刘 对,你有摄影的良好基础。
梁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,我也不敢这么说。基本的摄影技术、手段、构图等要知道,否则你也拍不了纪录片。
刘 在《房东蒋先生》中,整部片子充满着鲜明的对比,比如:一个上海男人与一个北京女人,一个生活在城市、充满小资情调的“老克勒”与一个穿越过战场、深入过青藏高原、只身闯荡过非洲、阿富汗的摄影师,还比如年龄、性别、语言、性格、生活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等等,你在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,意识到这种鲜明的对比性吗?意识到这是片子的亮点吗?
梁 意识到了,如果没意识到,我也不会对他感兴趣,这是首先意识到了的,因为这个人离我的距离太遥远了,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一个普通的日子捕捉住了这个人物。当时不管是下意识的,还是有意识的,我能住在那里,去揣摩他、观察他,肯定会直觉到这样的反差因素,这种反差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如果他是个北方老头,我可能不会感兴趣的。
刘 在片子里,你开始叫他蒋叔,后来叫他老头儿,而蒋先生把则你叫成“姑奶奶”,反差这么大的两个人在一起,怎么能够相融呢?
梁 我跟你说,一千个人里也难有我这样的,你知道我爱好什么吗?我最大的两个爱好就是,一喜欢去陌生的地方,二就是喜欢跟陌生的人打交道。但是,这次我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情绪上困难的。一开始我特别不习惯他,很烦他,说话嗲不啦叽的。我是个自由惯了的人,根本就不习惯整天回去后就面对这么一个没感情、没血缘的老人,还窝在那样的黑房子里,我一回去就发愁。所以,一开始连着有这么三、四天,本来晚上9点就该回去了,可我就是不想进去,那时这一带拆迁,也没什么酒吧,我就在马路边上走过来、走过去,能走一两个小时。看着那灯光我害怕,太阴森、太带有30年代的感觉,太格格不入,太压抑了,恨不得一进门就钻进被窝睡觉。根本不想跟他说话,明知道这个人物有意思,也不想拍他。
刘 后来,怎么融洽的?从开始两个人隔绝、生硬的状态,到后来俩人都变得很温和而互相牵挂,他半夜为你煮红茶,早上为你做三名治,用刷子连搅带戳地给你洗衣服,你送他衣服,为他请律师,跟他买来蛋糕“庆贺离别老洋房”,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转变?
梁 过了10来天,我就回北京了。当时,一上飞机,就觉得太好了,终于离开那儿了,我又开始了我熟悉而躁热的生活。可是,后来发现我好像有一点习惯了那个黑暗的灯光,有一点习惯了一个老人那种很静的生活。生活一躁热,我就想到他挺可怜的,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,他接电话时都快哭了,他说“一个人,觉得很无聊,觉得很没有意思”。可是真要让我回去,我还是不想回去,要不是电视台有事,我真不想回去。不过,走时我还是给他买了一件衣服。等我再回去的时候,他也给我买了一身棉睡衣,特便宜那种的,当然不是钱的问题,这是一份心意。很怪,临进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还不想进去,但真正进入以后觉得挺好的,觉得挺熟悉的,我又回来了,这是第二次。从那之后我对他就再也没有反感了,也没有对他看不惯了,就很适应了。然后到第三次再去的时候,特轻松,像回家。后来我发现,我跟他学了好多东西。
刘 你忽然意识到,这个人生活得很精细,是你原来不曾有过的?
梁 对,我学会了如何喝咖啡,辨别什么是好咖啡,为什么喝柠檬红茶,像他做的那么好的柠檬红茶,我再也没喝过。还有,为什么指甲不能剪,只能挫,要挫成什么形状,在他的指点下,当时在上海我留的指甲可漂亮了,这一回来就完蛋了。那次见面,他说“让我看看你的指甲”,我说“别看,早没了!”后来我已经跟纪实频道的人熟了,制片人王小龙就说,梁子别住老头儿那了,条件太差了,外面每天还施工,天冷了,暖气也没有,住酒店吧。我坚决不肯,我已经住习惯了,我每天早上走晚上回,老头每天给我做三明治,你看那画面上都有,做得特好。他做好多,我也吃不了,就带去,电视台很多人都吃过。
在一种冲撞中展现
刘 彼此的冲撞,构成了这部片子的另一个特点。一方面是蒋先生和这个社会的长期的冲撞;另一方面是蒋先生和你两个个体之间的冲撞,这些冲撞都跟这老宅有直接的关系。你在这冲撞中,如何处理主观介入和客观纪录这两种关系的?
梁 我没想那么复杂,很简单,我开始不烦他了,这是一个变化;再一个变化,就是我拍着拍着就不知道我在拍摄了,我的机器不是这么举着的,是这样夹在胳膊下的,我们俩说话的时候,或者他在做事的时候,我就把显示屏合上了,摄像机这么冲着他。我这个时候把摄像机用得特别顺手了。小机器,小有小的好处,也没考虑、分析什么该拍,什么不该拍,我是一有时间顺手拿着就拍,很自如。
刘 片子从一开始,就是满含火药味的“语言冲撞”,结束时,仍在同一景别中,却是一种满含牵挂的“语言冲撞”,你说你以后要一直关注他,他说你肯定漏气(不践约)。语言的冲撞,使你们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人形成了简单、直接、真实的关系,这是你一贯与人交往的方式,还是你有意用语言激他?
梁 我从始至终,从刚开始认识到现在,我没有故意做任何事情,一切都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。我当时喝了酒的,喝了半斤,说话特冲。因为,再过两天这老房子就要拆了,我也挺不舒服的,有点难受,不愿意离开那儿了,而且我对那个房子也习惯了,我现在在上海就觉得任何一家宾馆、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那个地方住得好了。那天晚上,我就跟制片人他们出去喝酒了,很晚了才回来。路上,他们提议跟老头买个蛋糕,夜里一、两点,店子大多都关门了,我们一路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。当时,老头心情也不好,我不让他睡觉,逼着他说话,他斜依着床头,我没拿机子,也没支架子,就把机子搁在那一摞被子上,所以推拉都没有。你注意到没有,他怕头发弄脏了床头,还拿一张报纸垫着呐。
刘 看画面上,蒋先生也显得很自然。
梁 我跟他一切都特别自然。我开着机器,跟他聊,他知道,后来他也无所谓了。他讲的好多自己过去的事,几几年干嘛干嘛,家里发生了什么事,好多素材都是我每次请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录的。吃饭前,我就先到卫生间把录音笔打开,放在我兜里,是这么聊的,因为我们中间要搁个录音的东西,他是不会说话的。其实我跟你说,我这个人是最不爱问别人的事了,而且不是说不爱问,根本就是不关心别人,因为我从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现在好多了。那天我们一帮朋友在批判我的时候还在说,说我这个人太自私,虽然挺大度,但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,根本不关心别人的事。可是到老头这儿,要采访他,要问他,这是我不太习惯的。后来干超把这些录音变成了解说词,找了一些历史资料作画面,还补拍了一些场景的镜头,请了话剧演员李家耀先生给老头的那几段内心独白配了音。
刘 有关你内心独白的那几段解说词,是你自己配的音吗?
梁 不是,我配音太恶心了。塞拉里昂的那个片子是我配的,紧张、生硬,简直不像我了。那次配音特逗,说非洲有一种树,凿一个洞,插一个管子进去,流出的液体发酵2小时后就变成酒了。本来是“清晨,男人们从树上取了这种酒,挑着大桶到镇上去卖……”,可我给念成了“清晨,男人们……挑着大粪桶到镇上去卖……”。嗨!当时,谁都没听出来,干超也没注意,后来才发现的。我那时配音特恶心。从此,坚决不配了。
刘 这个配音,跟你的感觉特别像,音质也特别像。
梁 是那个女演员杨坤给配的,干超找了很多人试过。
刘 还不错,张显了你的个性。不过我觉得,从你那部《跳吧,波尔卡》来看,还是应该由你自己配音比较好,这样自然并带有你自己鲜明的特色。多配几次,找到感觉就好了。当然,这里还有解说词的问题。
梁 是吗?
刘 我感觉,你在这部有关阿富汗国家的片子里,所写的解说词,丢了你自己,丢了很多感性的东西,用了不少概念性的语言,来大谈阿富汗的妇女问题,同时又叫别人来给你配音,看着像个长篇新闻报道,感觉有点飘。片子挺“忧国忧民”的,但它们遮蔽了你自己。你的第一部片子《非洲并不太远》,解说词虽然写得比较平实,像是非洲生活简介、科普说明,但是片子是由你自己来配音的,这与片中的你的所见所闻互相辉映,便显得自然而真切。当然,我不是说,所有纪录片人都应该自己配音。不是的,因为你的所有行为和片子,都构成了非常独特的你。这个独特的你应该和片子是一个整体的。现在干超正在剪辑的非洲红海岸边的这个片子,我建议你注意解说词的这个问题,尽量能自己配音。
梁 哎,你说得有道理。《跳吧,波尔卡》里的好多词是我从网上下载的,《非洲并不太远》是我直接从我的书里摘下来的。一切我都还在慢慢摸索。
就这样边学边拍
刘 我也只是一个感觉,一个建议。在《房东蒋先生》中,个性的你和你个性的语言,把沉郁多年的蒋先生的个性也给搅拌出来了。老房要拆的前一天,就是你喝酒回来那天晚上,老头儿竟也跟着你“疯闹”了一回,他猛踢着地上散乱丢弃的杂物,对于舍不得踢的东西,他又小心地拎到一边。而你在一边起哄,骂他窝囊。你不仅纪录了他,你也纪录了自己。这种“二元性”的纪录方式,对纪录片创作来说特别有启示意义。通常,许多拍纪录片的人是“躲”在后面不说话的,偶尔提问也会问得特别官腔,特别的四平八稳,像你这样的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张扬开来,生动地衬托出蒋先生的孤寂、怪异、细腻、温情的人性特征,这样的做法好像不是太多。这种方式是有意为之,还是自然形成的?
梁 问题是我不说话,他就不说话,他不说话我着急,我总得让他说呀,所以我跟平常一样地说。我根本不知道,我声音那么大,说话那么厉害,而且我已经不觉得我在拍他了。再一个我拍完干嘛,我还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用,也没想到怎么去公之于众,我手里的这些东西也不觉得是什么录音机、摄像机了,太自然、太自然地去纪录他了。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,录像不录像都是这样,说话的口气什么的,不可能是平时这样说话,一端机子就那样说话,我们不太可能是这样的。
刘 要纪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内心情绪,选择是非常重要的,考虑过这个问题吗?哪些该拍,哪些不该拍,特别是对细节的纪录,有什么样的纪录原则吗?
梁 我什么都拍,凡是我想到的。早上可以拍一点,从电视台回来可以拍一点,都是有空的时候拍的,你看好多画面都是晚上的,白天的很少。他的生活特别简单,他的生活就这样,日常生活就是这么点东西,没什么选择的了,该拍的都拍了,包括倒垃圾什么的,直到把想起来的东西都拍完了,我也该走了。
刘 你说你拍纪录片,没有那种规定性的东西在脑袋里,这很好。我在《房东蒋先生》里,看到你除了纪录人物之外,环境的交代拍得还挺地道的,比如说每天你是从冲击钻的噪音中醒来的,画面是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……
梁 有些画面是干超他们后来补拍的。对环境的交代,我也是学来的。就是我在剪非洲那个片子的时候,有个朋友,他原来是搞纪录片的,是上海人,偶然会来看看我们剪片子,他在一旁看着着急,总说“推呀!”、“特写!”、“周围环境交代,环境呢!”,他就在那儿骂我,我说下次跟我一块儿去,他说不,说我太笨了,真笨!说我是搞摄影的嘛,也应该明白!他骂我,我特高兴,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老拽着他,让他再给我说两句,他说看着着急,我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骂人,这在课堂上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是的,我也恨我自己,手抓住人,怎么不知道给个特写,真他妈笨!我一次不知道,两次还不知道吗?另外,别人怎么拍,我也看,然后把“发现”的东西拿过来用。我这一次拍非洲红海岸边的事,就特别注意环境的交代,特别注意抓拍特写。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刘 当然,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停地学习、感受的过程。对于特写的抓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手法,大连李汝建的纪录片《海路十八里》,全片一个特写都没有,他是有意为之的,他很注重纪录印象。所以,看别人的作品,不必简单学皮毛,要在鉴赏中找到自己的对应感。
梁 回头把片子给我看看。
刘 前后在老头那儿拍了多久,拍了多少素材?
梁 从2002年9月到2003年春节2月吧,先后去拍了三次,从老头穿T恤拍到老头穿皮夹克、牛仔的时候。中间一次是去给非洲的片子配音,最后一次是房子要拆了,老头打电话来,我就飞去了。一共拍了24盘。
刘 一盘多少分钟?
梁 30分钟,是DVCOM的带子。
刘 在你拍摄中遇到什么技术问题吗?怎么解决的?
梁 在塞拉里昂的片子里,好多地方只要照度不够,我“啪”就打到“增益”,正黑着的时候,“嘣”就亮了,糟糕透了。 后来做片子的时候,我特别感谢干超,他说你看你又开这个了,让它黑着没关系。老头儿这个片子就没用任何增益,他家里也黑。现在,我用150P就可以用白平衡了,我找了一个窍门,我先打到手动,在室内调好白平衡,到了室外就换到自动,从室外到室内,先自动,一到室内就换到手动,这样画面就不会闪了。好多东西就是这么一点、一点学来的。
无法明朗的创作关系
刘 为什么不自己做后期?遇到什么困难?
梁 我觉得,凡事不要样样都占全了,我是搞摄影的,拍纪录片只是副业,否则,精力不够不说,可能还什么都做不好了。后来,片子拍完,我走了,到阿富汗去了,就把所有素材丢给了干超。
刘 你一直跟干超合作得愉快吗?
梁 非常好。干超二十多岁吧,那时刚从英国回来,分到纪实频道。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的,他很用心,才气眼光都相当不错,他拍过一个片子叫《寂寞入口》,比较现代化。他拍年轻人拍得特别好,是一个挺有思想的人,话不多。他开始是叫梁子梁子,后来就叫老梁,我叫他“干煸”(干编),他跟别人不会这样的。他心里特有数,但不怎么爱说话。
刘 你和干超的合作,很有意思,是纪录片自由制作者和主流媒体制作者的碰撞,它或许会带来纪录片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,另外纪录片自由制作者也可能将被大众媒体同化,这两者从来都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,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?
梁 没想过太多。我觉得,有一类人拍纪录片,是为了要糊口的,所以他会特别关注他的片子是播还是不播,我不是说我不在乎,只是我没有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事情来做,我拍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要拍它?如何去播出?我就觉得无论到哪儿,拍片子不会浪费我的交往,就像咱俩在一起谈这事,没录音就会浪费。我平时在生活中就是这样,看电视的时候,我一边烫衣服、一边提臀,总是干好几件事情,如果只干一件事情,就觉得特别浪费时间。我一边拍照片,一边搞摄像,一块儿拍不是更有意思吗?而且两个不一样。至于播不播,后话!我拍了,我没浪费这个时间,我更有乐趣了,因为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,可以做好几样有乐趣、有意思的事。
刘 干超在后期补上了一些历史资料,以突出老上海的时代背景; 同时,用画外音的方式,把叙事的空间由同期声的交流、碰撞,扩展到历史的讲述和内心的独白。这样做,的确使纪实的零散、平面、单一状态得以粘合、拓展和延伸,增强了叙述的故事性。片子被干超做成现在这样,你想到了吗?
梁 我根本没想到这些素材能做成一个片子,能做成这样,现在就能播出来,还能做成中英文的,还能参赛,我太意外了!我以为要等老头找了个媳妇儿,结婚了,又生了个孩子之后,有了这样圆满的大结局,就可以完成我的片子了。所以,我总催老头赶快结婚,赶快生孩子。片子最后,我不是跟老头说,我会一直拍你、关注你,老头不信。老头说他不结婚,我还在想,那我的片子怎么完成呀!
刘 我感觉,这种方式有点像把一种原生态的东西放置到了一个精美的镜框里,粗放中有精致,是两种风格的结合,也是一种冲撞,你对这种结合满意吗? 你有没有自己的考虑?
梁 当时看完以后,有两点不是特别满意,一个是历史资料用得有点过多,再一个就是这个配音,太过了,不是很满意。
刘 为什么不满意?
梁 有点不自然,太艺术化了,我惟一感觉到不舒服的就是这个太艺术化了。
刘 拍了这么几个片子了,你现在再拍,有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,认为我要用什么什么方式去拍?在这过程中,有没有自己又形成了一些规定性的东西?
梁 我感觉,现在在拍的时候,后面还是有框框了,这个框框是自然形成的,可是你没有它也不行。这次我去红海边吧,有一点不太一样了,我到了村庄以后,不是见什么拍什么了,而是考虑得太周全了,妇女的来一个,海上打鱼的来一个,这个人家庭来一个,然后再弄一个儿童的……其实特别恶心,其实不好。
刘 为什么说这样不好?
梁 就是太框了,太板了,有意识把它分类分得特周全。当然,像以前那样逮着什么拍什么也不行。我觉得应该是,到了这个村庄之后,我得提炼出一个什么东西,反映一个什么东西,比如反映这个村的……腐败……黄牙,随便乱说的,那么所有的拍摄就应该是围绕着这个灵魂的。
专家的评述
刘景锜(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资深电视人):《房东蒋先生》对人的情绪作了比较充分、深刻的挖掘,超越了过去纪录片只着重“用国际的语言来讲中国的故事”的惯常做法,让一个上海“老克勒”尘封多年的惆怅、无奈、无助、怀旧、对未来茫然的情绪,在一个异性面前宣泄出来了,同时片子还展现了这位蒋先生为“屋”所累,又离不开“屋”的复杂情绪。当然,这其中所挖掘的不仅仅是一般人的情绪,而是一个上海人的情绪,有很强的地方特色。片子比较好的揭示了海派人物的性格,与那个在京派文化哺育下的有着传统的洒脱的敬大爷(《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》)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。梁子对上海人的挖掘,是上海编导们做不到的,这是一个北方见过世面而很泼辣的女子,从她对上海男人所具有的好奇和新鲜的感觉中挖掘出来的,是极大的反差造成的。极张扬的个性,搅乱了蒋先生的一潭死水,带来了一种预想不到的效果。这也通常是我们的编导做不到的,他们往往只在客观纪录着,那样的话蒋先生那种情绪化的东西或许就挖掘不出来了。片子还带有一点生活喜剧的味道。以往,中国人的生活被我们的纪录片拍得太沉重了。纪录片当然是要反映现实的,但现实并不仅仅意味着沉重,即使是沉重,里面也会有喜悦的东西,而喜悦的里面也会有眼泪。它给我们的启示是:不要就沉重论沉重,而要在沉重中找到欢乐,找到我们热爱生活的理由。我们纪录片应承担起这个责任。虽然,该片在节奏的安排、剪接的处理方面还略有不足,还不太成熟,比较粗糙,梁子个性的张扬也显得过分了一些,但我觉得有“毛边”的东西是最好的,不要太精致,不要太天衣无缝,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有“毛边”的,这样或许更本真,更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,我们不应苛求。因为,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生命力,可以听到一种襁褓中婴儿带着血污的哭声、叫声,这其实是很可贵的。
朱羽君(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):《房东蒋先生》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另类的介入方式,创作者利用了她与房东蒋先生相処的一段生活机遇,萌动了拍摄纪录他的兴趣,由于有近距离的接触,创作者与被摄对象建立起了非常生活化、人文化的平等关系,使她的纪录非常自然,非常随意。有意思的是,这两个人都很特殊,性格和价值观上有很大反差,蒋先生是位解放前资本家的“遗少”,长期的封闭,养成了冷峻孤僻的性格。而梁子则是一位非常现代,非常豪放,富有挑战性格的人,两种独特的个性相互碰撞,迸发出一串串生动的对话和饶有趣味的情节,使该片的素材具有很高的质量。另外该片的生产方式也很另类,梁子是搞图片摄影的,真正拍纪录片还是第一次,在创作中,不断得到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同行的鼓励和指点,并给予各方面的支持,编导于超不但在前期了解和商讨了素材的拍摄,在后期编辑上也下了很大功夫,对大量素材进行了筛选、整理,编得很流畅,素材的质量和编导的高水平发挥,使影片获得成功。现在的纪录片创作可以有更多的方式,这种非主流的,贴近生活的自然纪录,更好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纪实精神。创作者具有个性的介入方式,以及独立拍摄与专业编辑之间的合作方式,电视台与独立制片人之间的合作方式,都有助纪录片的多样化、个性化,使纪录片具有更多的另类特色,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,会使我们看到人的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活轨迹。
时间(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会副理事长 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):《房东蒋先生》打破了由摄像机建立起来的纪录片常规的主客观的关系,建立起了以性格和个人化方式才能构成的关系,创作者个性张扬得特别自然。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纪录方式,是非常个人化的,这其实已经不是拍摄方式了,而是一种沟通方式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视觉手段是如何深入到人的内心的,当然片中所展现的前提是,梁子首先不是在工作,而是在纪录她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梁子的创作是一种高级的艺术手法,就像美术活动中后来出现的行为艺术一样,她的片子有行为艺术的色彩。因为从视觉语言本身看,大部分都是缘于一种采写的语言的视角,不管哪种形式,总能感觉到你在观察别人,即使你被生活所感染,被所纪录的拍摄对象所吸引,也仍然难以逃出旁观者的角色。而梁子所给我们的更像是生活本身,它不是发表的文章,而是一篇自己的日记,当你打开了这个日记,一但进入这种情景当中,你的体会是很单纯的。这对我们的启示是,应该淡化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身份,进而降低功利色彩,你要被生活感动就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而不是去驾御生活。虽然她本人在经验、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,但她的创作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录方式。通常,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个性化的表现方式,而梁子的是个性化的纪录方式。她把个体与拍摄行为都纪录了进去了,这种突破纪录者本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,也是当代艺术要完成的课题。在现场,她的操作显得很随意,但实际她有比较好的图片摄影的功底,所以用DV这种手段也一样可以做得比较专业,镜头并不是显得很乱,从摇镜头到固定镜头都挺不错,有时她还挺困难的,又要说话又要拍摄,就是搞专业的也不见得能把握得好。当然,她的纪录是流程性的,只能给人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。所以说,《房东蒋先生》的成功还得益于编导干超,他辑编得不错。
编辑之眼 (郭际生,《南方电视学刊》总编助理,本文编辑)
毫无疑问,《房东蒋先生》是一部纪录片,但我同时也觉得是一部故事片,片名叫做《老洋楼里,蒋博士遇上了姑奶奶》,这已表明了我对它的喜爱。说它纪录,它把生活和人物所推到的近景,是少见的。说它“故事”,在一个小时里,对人物及相关故事叙说得层次匀称起伏,情趣和况味俱足(一个变简为繁,一个化繁为简,两种性格立现)。加上片中电影语言的娴熟(指片中“嵌入”式情景),幼稚镜头的恰到好处,历史时空的跨度,人物个性的忒独,实在令我惊殊。外显的是两条情绪结构线,前半是蒋先生的情趣,后半是由此延展出来的况味。内藏的是二人的对话结构体。看着看着,在为鲜活真实而感触,又为有些“缺漏”而惋惜。愿提出来与作者、方家览教:一是人物的藏和露,假如这样安排,梁子一直只是问,只出声音,不露真人,只靠直率语言与房东拌嘴、碰撞、磨合,结尾才现真身;而蒋先生人声俱显,一明一暗,更有“悬念”,情绪更见“饱满”,便于注意力的观看,情趣和况味会更“全”。说不定,这可以成为另一部非克隆的《英与白》,因为,纪实里,也不妨以艺术手法营造效果。二是人物旁白的失策,仿真人物的自述,在片里并不给人真实和熨贴。因为是编的,而大活人就在眼前,感觉便隔了。只说临尾处,蒋先生站在凉台俯看着那棵白玉兰,画外音是仿声:“我的白玉兰就要开了,今年会开多少呢?五百朵,一千朵,还是两千朵?……但我看不到了。”这话,要是改为弃仿声,用真声,即前面蒋的“这树也带不走。开的超过五百至一千朵。”现在的画面里,已经是很现在的契合了:蒋俯看树,树摇下来时蒋下楼来,转头抬眼一望,切到树,再复用蒋的前话:“白玉兰开过就是樱花了,也没有叶子……”,最后蒋关上大铁门,走出去的背影(镜头再长点更佳)。老白玉兰树的四次出现,都与人物的境遇、心情相连,正可由此深邃起内涵。景语皆情语,去生硬,感真情,水乳更可得交融。
访谈后记
希望以上呈现给读者的,是一个真实梁子的个性和述说,是一个能引发纪录片人对既定规则的思索,是一截纪录片实践中有探索价值的现象,是生活本身的存在与发现眼睛的慧悟之融合(既指片子本身,又直片子所给予)生活也好艺术也罢,世相岂有完美,但求有玩味、有动感、有触发、有理想的追求,有现实的洞察,有拳拳之诚和赤子之心。
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博士生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
——2009-04-20 12:19:42,4444上传
刘 说来也巧,我的上一个访谈,是在大连做的,所谈的内容也是涉及到“老宅”的拆迁,那个片子纪录了老宅里拆迁户的群体印象,而《房东蒋先生》纪录的是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心里感受。你是先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,还是租住了这个房子之后才发现了他?
梁 2002年夏末,因为我要跟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,剪我的那部去塞拉里昂拍的片子。住酒店的话,费用太大,有个朋友就说找个地方给我住。他说他认识一个老头儿,老头儿有17间房子,三层楼,就他一个人,没结婚,也没工作过,到时给他些钱,他家离电视台大概走十分钟就到。只是老头儿有点怪,希望我跟老头儿处好一点,别跟他闹意见。当时我也没多想,他有17间房子,这么大,怎么住我也不会打搅他呀。
刘 后来呢?
梁 我到上海后,带着行李跟朋友就去了。去之前,我们跟老头儿打了电话,到了老头儿家外面,看到周围正在拆迁,朋友说老头儿出来迎接你了,我当时一看,呀!老头儿穿着特白的衬衣,雪白雪白的,灰色的西装,烫得特别平整,头发弄得一丝不乱,油头粉面的,这么精神个老头儿!这么讲究的老头儿!心想家里一定特干净、特好,那些房子也满满当当的像客房一样的。我挺高兴跟他上去了。开了门,破铁门咣咣的,一层什么东西都没有,空的,二层,只有几个破椅子,到了三层一看,整个一个垃圾场,因为他要搬迁嘛,东西全用一些小纸盒子装着,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破破烂烂的,有几件小家具,破床、破电视机,在那还树着个梯子什么的,他家墙上还被凿了个大洞,外面还传来很大的冲击钻的声音,“得哑——”的,特吵、特乱。
刘 那你没有立即走掉?
梁 我一进去,朋友就跟我道歉说,梁子对不起,我不知到这里要拆迁,咱们不住了,重新找个地方,又没床什么的,怎么住呀。但我一想,老头儿反差这么大,这房子上来的时候,是摇摇晃晃的感觉,再回头一看老头儿,那么西装革履的,那么笔挺的,简直跟这个房子格格不入!其实,这时我根本没想到会拍什么,我就是有一种好奇,我就说,不走了,我不走了!老头儿其实也不是特想让我住,说没床什么的,我说铺个垫子,地铺也可以。老头儿特别不情愿地找了个垫子。当时,屋里面特乱,全是土,特乱、特脏。等我晚上从电视台回来,灯光很黑暗,放着周璇的歌,老头儿已经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,一个带扶手的简易沙发上铺着白毛巾。一想我这是在大上海,一想不远处就能看到的锦江饭店,我看着那白毛巾,就特来气,我特别忌妒地说,你把它打扫了干什么!你换成白毛巾干什么!老头一看我特厉害,说客人来了总要打扫干净的呀!然后,我们也没什么话说,我也根本没想到要拍什么片子。
刘 当时没想到,但是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想要拍他的?
梁 很快。第二天,我去电视台跟他们说了这个怪老头儿,反差大,老房子里总有30年代的感觉,可房子又要拆迁,他已经是个“钉子户“了。我也直觉到,单从这些,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东西,但究竟有什么,还不知道,同时也在犹豫,是单纯拍照片,还是拍片子,我还没想好。电视台的人听了以后就说:“赶快拍片子呀!”我当即决定拍片子了。
刘 你当时带着你的PD100AP?
梁 我当时是带了这个机器来上海的,要没带也不会拍了。
个性张扬的自然纪录
刘 从介绍你的文章中来看,你一直关注的是城市之外的人和事,这次怎么把关注点落在了最具城市特色的上海,落在了最具上海人特色的蒋先生身上?看来,你关注的兴趣点不仅仅是以地域来划分的,那么,这个兴趣点是由什么来确定的?在什么情景下,你萌发了要纪录房东蒋先生的念头?
梁 我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只觉得他挺怪的,反差太大,特别想了解他,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,当然我之所以能拍成他,也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,也是挺好奇的,而且我这人是个见面自来熟,才去一两天很快我们就搞得特熟。但实际上我特痛苦,我根本就不愿进他家,因为他家靠近锦江饭店,锦江饭店是个五星级的,特豪华,上海电视台也是高楼大厦,里面条件特别好,是全国一流的。可我来到上海,窝在这么一个地方,心里特不痛快。
刘 当时没想到去跟电视台借个机器,请人来跟你拍?
梁 没想。我当时想的就是,即使拍,也不能打搅老头儿太多的生活,我能感觉到老头儿是个非常安静的人,我本人也刚住进那里,而我和电视台的人也不熟,又是第一次合作。我没接触过老头儿这样的人,老头也没接触过我这样的人,他爱安静,我本身又躁得慌,如果我再带人来拍,乱乱哄哄,这绝对不现实。老头不喜欢的人,他都不让进门。最后,我都跟他特熟了,曾经带过两个人来,他很勉强,不屑一顾,他很傲。
刘 你一开始就想清楚怎么拍了吗?
梁 没有,没想,不太明确。拍老头,是顺手拍的。那时我一早就到上海电视台去跟干超他们一起剪我那部非洲的片子,我就会跟他们说,昨天拍的什么什么,人家就问怎么拍的,我就说怎么怎么拍的,人家就说要这样、要那样。我老是恶心老头儿,讲老头儿的笑话,什么呀一个破牙膏皮还擀了又擀的,他们说这个情节太好了,应该拍,一个摄像也不停地说怎么怎么拍。另外,他们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,说梁子你一定要抓住这个题材,因为这样的事、这样的人特少,很难得。
刘 在拍《房东蒋先生》时,脑子里有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,什么叫纪录片,纪录片应该怎么拍?
梁 没有,我现在都没有。你现在要让我说什么是纪录片,纪录片该怎么拍,我也不知道。
刘 那在你的直觉中,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的?
梁 我只觉得纪录片,就是纪实性要强,是真实的,当然我觉得手法是最重要的,如果中国有10样,世界上就应该有50样,而且还有其他超过50样的,你还可再搞定51样,也无所谓。但它一定是真实的、不是去摆的、不是虚构的,仅此而已,就够了,只要这个事是真实的,完整不完整,有没有前因后果,都没关系,但只要它是真实的就可以了。至于手法,是不是纪录片的手法,还是什么什么手法,都可以,访谈也是纪实手法,它也是一个手法,一个方式。
刘 关于真实问题我们在这不讨论,顺你这个意思,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按照一些固定的框框去拍纪录片,那你怎么会自觉意识到这一点?
梁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,因为摄影。因为我在摄影上已经走过了那种必须按规定性、规则性的东西去拍的过程,一想我就觉得特别恶心,但我想跳却很难跳出来。所以,我拍纪录片的时候,就再不想这样做了,再不要手把手去学,再不希望从什么书去学了,我不想知道什么规则,因为你知道有了规则,要打破它就太难了,与其你要打破它,还不如不想知道它。当然,最基本的拍摄是有规则的,比如推拉摇移,我过去不知道,现在我知道了,还可以停,还可以怎么怎么的,所以知道一点就够了,剩下的构图、用光等就是摄影的手段了。
刘 对,你有摄影的良好基础。
梁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,我也不敢这么说。基本的摄影技术、手段、构图等要知道,否则你也拍不了纪录片。
刘 在《房东蒋先生》中,整部片子充满着鲜明的对比,比如:一个上海男人与一个北京女人,一个生活在城市、充满小资情调的“老克勒”与一个穿越过战场、深入过青藏高原、只身闯荡过非洲、阿富汗的摄影师,还比如年龄、性别、语言、性格、生活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等等,你在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,意识到这种鲜明的对比性吗?意识到这是片子的亮点吗?
梁 意识到了,如果没意识到,我也不会对他感兴趣,这是首先意识到了的,因为这个人离我的距离太遥远了,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一个普通的日子捕捉住了这个人物。当时不管是下意识的,还是有意识的,我能住在那里,去揣摩他、观察他,肯定会直觉到这样的反差因素,这种反差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如果他是个北方老头,我可能不会感兴趣的。
刘 在片子里,你开始叫他蒋叔,后来叫他老头儿,而蒋先生把则你叫成“姑奶奶”,反差这么大的两个人在一起,怎么能够相融呢?
梁 我跟你说,一千个人里也难有我这样的,你知道我爱好什么吗?我最大的两个爱好就是,一喜欢去陌生的地方,二就是喜欢跟陌生的人打交道。但是,这次我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情绪上困难的。一开始我特别不习惯他,很烦他,说话嗲不啦叽的。我是个自由惯了的人,根本就不习惯整天回去后就面对这么一个没感情、没血缘的老人,还窝在那样的黑房子里,我一回去就发愁。所以,一开始连着有这么三、四天,本来晚上9点就该回去了,可我就是不想进去,那时这一带拆迁,也没什么酒吧,我就在马路边上走过来、走过去,能走一两个小时。看着那灯光我害怕,太阴森、太带有30年代的感觉,太格格不入,太压抑了,恨不得一进门就钻进被窝睡觉。根本不想跟他说话,明知道这个人物有意思,也不想拍他。
刘 后来,怎么融洽的?从开始两个人隔绝、生硬的状态,到后来俩人都变得很温和而互相牵挂,他半夜为你煮红茶,早上为你做三名治,用刷子连搅带戳地给你洗衣服,你送他衣服,为他请律师,跟他买来蛋糕“庆贺离别老洋房”,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转变?
梁 过了10来天,我就回北京了。当时,一上飞机,就觉得太好了,终于离开那儿了,我又开始了我熟悉而躁热的生活。可是,后来发现我好像有一点习惯了那个黑暗的灯光,有一点习惯了一个老人那种很静的生活。生活一躁热,我就想到他挺可怜的,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,他接电话时都快哭了,他说“一个人,觉得很无聊,觉得很没有意思”。可是真要让我回去,我还是不想回去,要不是电视台有事,我真不想回去。不过,走时我还是给他买了一件衣服。等我再回去的时候,他也给我买了一身棉睡衣,特便宜那种的,当然不是钱的问题,这是一份心意。很怪,临进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还不想进去,但真正进入以后觉得挺好的,觉得挺熟悉的,我又回来了,这是第二次。从那之后我对他就再也没有反感了,也没有对他看不惯了,就很适应了。然后到第三次再去的时候,特轻松,像回家。后来我发现,我跟他学了好多东西。
刘 你忽然意识到,这个人生活得很精细,是你原来不曾有过的?
梁 对,我学会了如何喝咖啡,辨别什么是好咖啡,为什么喝柠檬红茶,像他做的那么好的柠檬红茶,我再也没喝过。还有,为什么指甲不能剪,只能挫,要挫成什么形状,在他的指点下,当时在上海我留的指甲可漂亮了,这一回来就完蛋了。那次见面,他说“让我看看你的指甲”,我说“别看,早没了!”后来我已经跟纪实频道的人熟了,制片人王小龙就说,梁子别住老头儿那了,条件太差了,外面每天还施工,天冷了,暖气也没有,住酒店吧。我坚决不肯,我已经住习惯了,我每天早上走晚上回,老头每天给我做三明治,你看那画面上都有,做得特好。他做好多,我也吃不了,就带去,电视台很多人都吃过。
在一种冲撞中展现
刘 彼此的冲撞,构成了这部片子的另一个特点。一方面是蒋先生和这个社会的长期的冲撞;另一方面是蒋先生和你两个个体之间的冲撞,这些冲撞都跟这老宅有直接的关系。你在这冲撞中,如何处理主观介入和客观纪录这两种关系的?
梁 我没想那么复杂,很简单,我开始不烦他了,这是一个变化;再一个变化,就是我拍着拍着就不知道我在拍摄了,我的机器不是这么举着的,是这样夹在胳膊下的,我们俩说话的时候,或者他在做事的时候,我就把显示屏合上了,摄像机这么冲着他。我这个时候把摄像机用得特别顺手了。小机器,小有小的好处,也没考虑、分析什么该拍,什么不该拍,我是一有时间顺手拿着就拍,很自如。
刘 片子从一开始,就是满含火药味的“语言冲撞”,结束时,仍在同一景别中,却是一种满含牵挂的“语言冲撞”,你说你以后要一直关注他,他说你肯定漏气(不践约)。语言的冲撞,使你们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人形成了简单、直接、真实的关系,这是你一贯与人交往的方式,还是你有意用语言激他?
梁 我从始至终,从刚开始认识到现在,我没有故意做任何事情,一切都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。我当时喝了酒的,喝了半斤,说话特冲。因为,再过两天这老房子就要拆了,我也挺不舒服的,有点难受,不愿意离开那儿了,而且我对那个房子也习惯了,我现在在上海就觉得任何一家宾馆、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那个地方住得好了。那天晚上,我就跟制片人他们出去喝酒了,很晚了才回来。路上,他们提议跟老头买个蛋糕,夜里一、两点,店子大多都关门了,我们一路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。当时,老头心情也不好,我不让他睡觉,逼着他说话,他斜依着床头,我没拿机子,也没支架子,就把机子搁在那一摞被子上,所以推拉都没有。你注意到没有,他怕头发弄脏了床头,还拿一张报纸垫着呐。
刘 看画面上,蒋先生也显得很自然。
梁 我跟他一切都特别自然。我开着机器,跟他聊,他知道,后来他也无所谓了。他讲的好多自己过去的事,几几年干嘛干嘛,家里发生了什么事,好多素材都是我每次请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录的。吃饭前,我就先到卫生间把录音笔打开,放在我兜里,是这么聊的,因为我们中间要搁个录音的东西,他是不会说话的。其实我跟你说,我这个人是最不爱问别人的事了,而且不是说不爱问,根本就是不关心别人,因为我从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现在好多了。那天我们一帮朋友在批判我的时候还在说,说我这个人太自私,虽然挺大度,但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,根本不关心别人的事。可是到老头这儿,要采访他,要问他,这是我不太习惯的。后来干超把这些录音变成了解说词,找了一些历史资料作画面,还补拍了一些场景的镜头,请了话剧演员李家耀先生给老头的那几段内心独白配了音。
刘 有关你内心独白的那几段解说词,是你自己配的音吗?
梁 不是,我配音太恶心了。塞拉里昂的那个片子是我配的,紧张、生硬,简直不像我了。那次配音特逗,说非洲有一种树,凿一个洞,插一个管子进去,流出的液体发酵2小时后就变成酒了。本来是“清晨,男人们从树上取了这种酒,挑着大桶到镇上去卖……”,可我给念成了“清晨,男人们……挑着大粪桶到镇上去卖……”。嗨!当时,谁都没听出来,干超也没注意,后来才发现的。我那时配音特恶心。从此,坚决不配了。
刘 这个配音,跟你的感觉特别像,音质也特别像。
梁 是那个女演员杨坤给配的,干超找了很多人试过。
刘 还不错,张显了你的个性。不过我觉得,从你那部《跳吧,波尔卡》来看,还是应该由你自己配音比较好,这样自然并带有你自己鲜明的特色。多配几次,找到感觉就好了。当然,这里还有解说词的问题。
梁 是吗?
刘 我感觉,你在这部有关阿富汗国家的片子里,所写的解说词,丢了你自己,丢了很多感性的东西,用了不少概念性的语言,来大谈阿富汗的妇女问题,同时又叫别人来给你配音,看着像个长篇新闻报道,感觉有点飘。片子挺“忧国忧民”的,但它们遮蔽了你自己。你的第一部片子《非洲并不太远》,解说词虽然写得比较平实,像是非洲生活简介、科普说明,但是片子是由你自己来配音的,这与片中的你的所见所闻互相辉映,便显得自然而真切。当然,我不是说,所有纪录片人都应该自己配音。不是的,因为你的所有行为和片子,都构成了非常独特的你。这个独特的你应该和片子是一个整体的。现在干超正在剪辑的非洲红海岸边的这个片子,我建议你注意解说词的这个问题,尽量能自己配音。
梁 哎,你说得有道理。《跳吧,波尔卡》里的好多词是我从网上下载的,《非洲并不太远》是我直接从我的书里摘下来的。一切我都还在慢慢摸索。
就这样边学边拍
刘 我也只是一个感觉,一个建议。在《房东蒋先生》中,个性的你和你个性的语言,把沉郁多年的蒋先生的个性也给搅拌出来了。老房要拆的前一天,就是你喝酒回来那天晚上,老头儿竟也跟着你“疯闹”了一回,他猛踢着地上散乱丢弃的杂物,对于舍不得踢的东西,他又小心地拎到一边。而你在一边起哄,骂他窝囊。你不仅纪录了他,你也纪录了自己。这种“二元性”的纪录方式,对纪录片创作来说特别有启示意义。通常,许多拍纪录片的人是“躲”在后面不说话的,偶尔提问也会问得特别官腔,特别的四平八稳,像你这样的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张扬开来,生动地衬托出蒋先生的孤寂、怪异、细腻、温情的人性特征,这样的做法好像不是太多。这种方式是有意为之,还是自然形成的?
梁 问题是我不说话,他就不说话,他不说话我着急,我总得让他说呀,所以我跟平常一样地说。我根本不知道,我声音那么大,说话那么厉害,而且我已经不觉得我在拍他了。再一个我拍完干嘛,我还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用,也没想到怎么去公之于众,我手里的这些东西也不觉得是什么录音机、摄像机了,太自然、太自然地去纪录他了。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,录像不录像都是这样,说话的口气什么的,不可能是平时这样说话,一端机子就那样说话,我们不太可能是这样的。
刘 要纪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内心情绪,选择是非常重要的,考虑过这个问题吗?哪些该拍,哪些不该拍,特别是对细节的纪录,有什么样的纪录原则吗?
梁 我什么都拍,凡是我想到的。早上可以拍一点,从电视台回来可以拍一点,都是有空的时候拍的,你看好多画面都是晚上的,白天的很少。他的生活特别简单,他的生活就这样,日常生活就是这么点东西,没什么选择的了,该拍的都拍了,包括倒垃圾什么的,直到把想起来的东西都拍完了,我也该走了。
刘 你说你拍纪录片,没有那种规定性的东西在脑袋里,这很好。我在《房东蒋先生》里,看到你除了纪录人物之外,环境的交代拍得还挺地道的,比如说每天你是从冲击钻的噪音中醒来的,画面是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……
梁 有些画面是干超他们后来补拍的。对环境的交代,我也是学来的。就是我在剪非洲那个片子的时候,有个朋友,他原来是搞纪录片的,是上海人,偶然会来看看我们剪片子,他在一旁看着着急,总说“推呀!”、“特写!”、“周围环境交代,环境呢!”,他就在那儿骂我,我说下次跟我一块儿去,他说不,说我太笨了,真笨!说我是搞摄影的嘛,也应该明白!他骂我,我特高兴,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老拽着他,让他再给我说两句,他说看着着急,我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骂人,这在课堂上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是的,我也恨我自己,手抓住人,怎么不知道给个特写,真他妈笨!我一次不知道,两次还不知道吗?另外,别人怎么拍,我也看,然后把“发现”的东西拿过来用。我这一次拍非洲红海岸边的事,就特别注意环境的交代,特别注意抓拍特写。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刘 当然,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停地学习、感受的过程。对于特写的抓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手法,大连李汝建的纪录片《海路十八里》,全片一个特写都没有,他是有意为之的,他很注重纪录印象。所以,看别人的作品,不必简单学皮毛,要在鉴赏中找到自己的对应感。
梁 回头把片子给我看看。
刘 前后在老头那儿拍了多久,拍了多少素材?
梁 从2002年9月到2003年春节2月吧,先后去拍了三次,从老头穿T恤拍到老头穿皮夹克、牛仔的时候。中间一次是去给非洲的片子配音,最后一次是房子要拆了,老头打电话来,我就飞去了。一共拍了24盘。
刘 一盘多少分钟?
梁 30分钟,是DVCOM的带子。
刘 在你拍摄中遇到什么技术问题吗?怎么解决的?
梁 在塞拉里昂的片子里,好多地方只要照度不够,我“啪”就打到“增益”,正黑着的时候,“嘣”就亮了,糟糕透了。 后来做片子的时候,我特别感谢干超,他说你看你又开这个了,让它黑着没关系。老头儿这个片子就没用任何增益,他家里也黑。现在,我用150P就可以用白平衡了,我找了一个窍门,我先打到手动,在室内调好白平衡,到了室外就换到自动,从室外到室内,先自动,一到室内就换到手动,这样画面就不会闪了。好多东西就是这么一点、一点学来的。
无法明朗的创作关系
刘 为什么不自己做后期?遇到什么困难?
梁 我觉得,凡事不要样样都占全了,我是搞摄影的,拍纪录片只是副业,否则,精力不够不说,可能还什么都做不好了。后来,片子拍完,我走了,到阿富汗去了,就把所有素材丢给了干超。
刘 你一直跟干超合作得愉快吗?
梁 非常好。干超二十多岁吧,那时刚从英国回来,分到纪实频道。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的,他很用心,才气眼光都相当不错,他拍过一个片子叫《寂寞入口》,比较现代化。他拍年轻人拍得特别好,是一个挺有思想的人,话不多。他开始是叫梁子梁子,后来就叫老梁,我叫他“干煸”(干编),他跟别人不会这样的。他心里特有数,但不怎么爱说话。
刘 你和干超的合作,很有意思,是纪录片自由制作者和主流媒体制作者的碰撞,它或许会带来纪录片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,另外纪录片自由制作者也可能将被大众媒体同化,这两者从来都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,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?
梁 没想过太多。我觉得,有一类人拍纪录片,是为了要糊口的,所以他会特别关注他的片子是播还是不播,我不是说我不在乎,只是我没有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事情来做,我拍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要拍它?如何去播出?我就觉得无论到哪儿,拍片子不会浪费我的交往,就像咱俩在一起谈这事,没录音就会浪费。我平时在生活中就是这样,看电视的时候,我一边烫衣服、一边提臀,总是干好几件事情,如果只干一件事情,就觉得特别浪费时间。我一边拍照片,一边搞摄像,一块儿拍不是更有意思吗?而且两个不一样。至于播不播,后话!我拍了,我没浪费这个时间,我更有乐趣了,因为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,可以做好几样有乐趣、有意思的事。
刘 干超在后期补上了一些历史资料,以突出老上海的时代背景; 同时,用画外音的方式,把叙事的空间由同期声的交流、碰撞,扩展到历史的讲述和内心的独白。这样做,的确使纪实的零散、平面、单一状态得以粘合、拓展和延伸,增强了叙述的故事性。片子被干超做成现在这样,你想到了吗?
梁 我根本没想到这些素材能做成一个片子,能做成这样,现在就能播出来,还能做成中英文的,还能参赛,我太意外了!我以为要等老头找了个媳妇儿,结婚了,又生了个孩子之后,有了这样圆满的大结局,就可以完成我的片子了。所以,我总催老头赶快结婚,赶快生孩子。片子最后,我不是跟老头说,我会一直拍你、关注你,老头不信。老头说他不结婚,我还在想,那我的片子怎么完成呀!
刘 我感觉,这种方式有点像把一种原生态的东西放置到了一个精美的镜框里,粗放中有精致,是两种风格的结合,也是一种冲撞,你对这种结合满意吗? 你有没有自己的考虑?
梁 当时看完以后,有两点不是特别满意,一个是历史资料用得有点过多,再一个就是这个配音,太过了,不是很满意。
刘 为什么不满意?
梁 有点不自然,太艺术化了,我惟一感觉到不舒服的就是这个太艺术化了。
刘 拍了这么几个片子了,你现在再拍,有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,认为我要用什么什么方式去拍?在这过程中,有没有自己又形成了一些规定性的东西?
梁 我感觉,现在在拍的时候,后面还是有框框了,这个框框是自然形成的,可是你没有它也不行。这次我去红海边吧,有一点不太一样了,我到了村庄以后,不是见什么拍什么了,而是考虑得太周全了,妇女的来一个,海上打鱼的来一个,这个人家庭来一个,然后再弄一个儿童的……其实特别恶心,其实不好。
刘 为什么说这样不好?
梁 就是太框了,太板了,有意识把它分类分得特周全。当然,像以前那样逮着什么拍什么也不行。我觉得应该是,到了这个村庄之后,我得提炼出一个什么东西,反映一个什么东西,比如反映这个村的……腐败……黄牙,随便乱说的,那么所有的拍摄就应该是围绕着这个灵魂的。
专家的评述
刘景锜(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资深电视人):《房东蒋先生》对人的情绪作了比较充分、深刻的挖掘,超越了过去纪录片只着重“用国际的语言来讲中国的故事”的惯常做法,让一个上海“老克勒”尘封多年的惆怅、无奈、无助、怀旧、对未来茫然的情绪,在一个异性面前宣泄出来了,同时片子还展现了这位蒋先生为“屋”所累,又离不开“屋”的复杂情绪。当然,这其中所挖掘的不仅仅是一般人的情绪,而是一个上海人的情绪,有很强的地方特色。片子比较好的揭示了海派人物的性格,与那个在京派文化哺育下的有着传统的洒脱的敬大爷(《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》)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。梁子对上海人的挖掘,是上海编导们做不到的,这是一个北方见过世面而很泼辣的女子,从她对上海男人所具有的好奇和新鲜的感觉中挖掘出来的,是极大的反差造成的。极张扬的个性,搅乱了蒋先生的一潭死水,带来了一种预想不到的效果。这也通常是我们的编导做不到的,他们往往只在客观纪录着,那样的话蒋先生那种情绪化的东西或许就挖掘不出来了。片子还带有一点生活喜剧的味道。以往,中国人的生活被我们的纪录片拍得太沉重了。纪录片当然是要反映现实的,但现实并不仅仅意味着沉重,即使是沉重,里面也会有喜悦的东西,而喜悦的里面也会有眼泪。它给我们的启示是:不要就沉重论沉重,而要在沉重中找到欢乐,找到我们热爱生活的理由。我们纪录片应承担起这个责任。虽然,该片在节奏的安排、剪接的处理方面还略有不足,还不太成熟,比较粗糙,梁子个性的张扬也显得过分了一些,但我觉得有“毛边”的东西是最好的,不要太精致,不要太天衣无缝,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有“毛边”的,这样或许更本真,更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,我们不应苛求。因为,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生命力,可以听到一种襁褓中婴儿带着血污的哭声、叫声,这其实是很可贵的。
朱羽君(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):《房东蒋先生》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另类的介入方式,创作者利用了她与房东蒋先生相処的一段生活机遇,萌动了拍摄纪录他的兴趣,由于有近距离的接触,创作者与被摄对象建立起了非常生活化、人文化的平等关系,使她的纪录非常自然,非常随意。有意思的是,这两个人都很特殊,性格和价值观上有很大反差,蒋先生是位解放前资本家的“遗少”,长期的封闭,养成了冷峻孤僻的性格。而梁子则是一位非常现代,非常豪放,富有挑战性格的人,两种独特的个性相互碰撞,迸发出一串串生动的对话和饶有趣味的情节,使该片的素材具有很高的质量。另外该片的生产方式也很另类,梁子是搞图片摄影的,真正拍纪录片还是第一次,在创作中,不断得到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同行的鼓励和指点,并给予各方面的支持,编导于超不但在前期了解和商讨了素材的拍摄,在后期编辑上也下了很大功夫,对大量素材进行了筛选、整理,编得很流畅,素材的质量和编导的高水平发挥,使影片获得成功。现在的纪录片创作可以有更多的方式,这种非主流的,贴近生活的自然纪录,更好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纪实精神。创作者具有个性的介入方式,以及独立拍摄与专业编辑之间的合作方式,电视台与独立制片人之间的合作方式,都有助纪录片的多样化、个性化,使纪录片具有更多的另类特色,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,会使我们看到人的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活轨迹。
时间(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会副理事长 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):《房东蒋先生》打破了由摄像机建立起来的纪录片常规的主客观的关系,建立起了以性格和个人化方式才能构成的关系,创作者个性张扬得特别自然。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纪录方式,是非常个人化的,这其实已经不是拍摄方式了,而是一种沟通方式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视觉手段是如何深入到人的内心的,当然片中所展现的前提是,梁子首先不是在工作,而是在纪录她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梁子的创作是一种高级的艺术手法,就像美术活动中后来出现的行为艺术一样,她的片子有行为艺术的色彩。因为从视觉语言本身看,大部分都是缘于一种采写的语言的视角,不管哪种形式,总能感觉到你在观察别人,即使你被生活所感染,被所纪录的拍摄对象所吸引,也仍然难以逃出旁观者的角色。而梁子所给我们的更像是生活本身,它不是发表的文章,而是一篇自己的日记,当你打开了这个日记,一但进入这种情景当中,你的体会是很单纯的。这对我们的启示是,应该淡化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身份,进而降低功利色彩,你要被生活感动就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而不是去驾御生活。虽然她本人在经验、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,但她的创作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录方式。通常,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个性化的表现方式,而梁子的是个性化的纪录方式。她把个体与拍摄行为都纪录了进去了,这种突破纪录者本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,也是当代艺术要完成的课题。在现场,她的操作显得很随意,但实际她有比较好的图片摄影的功底,所以用DV这种手段也一样可以做得比较专业,镜头并不是显得很乱,从摇镜头到固定镜头都挺不错,有时她还挺困难的,又要说话又要拍摄,就是搞专业的也不见得能把握得好。当然,她的纪录是流程性的,只能给人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。所以说,《房东蒋先生》的成功还得益于编导干超,他辑编得不错。
编辑之眼 (郭际生,《南方电视学刊》总编助理,本文编辑)
毫无疑问,《房东蒋先生》是一部纪录片,但我同时也觉得是一部故事片,片名叫做《老洋楼里,蒋博士遇上了姑奶奶》,这已表明了我对它的喜爱。说它纪录,它把生活和人物所推到的近景,是少见的。说它“故事”,在一个小时里,对人物及相关故事叙说得层次匀称起伏,情趣和况味俱足(一个变简为繁,一个化繁为简,两种性格立现)。加上片中电影语言的娴熟(指片中“嵌入”式情景),幼稚镜头的恰到好处,历史时空的跨度,人物个性的忒独,实在令我惊殊。外显的是两条情绪结构线,前半是蒋先生的情趣,后半是由此延展出来的况味。内藏的是二人的对话结构体。看着看着,在为鲜活真实而感触,又为有些“缺漏”而惋惜。愿提出来与作者、方家览教:一是人物的藏和露,假如这样安排,梁子一直只是问,只出声音,不露真人,只靠直率语言与房东拌嘴、碰撞、磨合,结尾才现真身;而蒋先生人声俱显,一明一暗,更有“悬念”,情绪更见“饱满”,便于注意力的观看,情趣和况味会更“全”。说不定,这可以成为另一部非克隆的《英与白》,因为,纪实里,也不妨以艺术手法营造效果。二是人物旁白的失策,仿真人物的自述,在片里并不给人真实和熨贴。因为是编的,而大活人就在眼前,感觉便隔了。只说临尾处,蒋先生站在凉台俯看着那棵白玉兰,画外音是仿声:“我的白玉兰就要开了,今年会开多少呢?五百朵,一千朵,还是两千朵?……但我看不到了。”这话,要是改为弃仿声,用真声,即前面蒋的“这树也带不走。开的超过五百至一千朵。”现在的画面里,已经是很现在的契合了:蒋俯看树,树摇下来时蒋下楼来,转头抬眼一望,切到树,再复用蒋的前话:“白玉兰开过就是樱花了,也没有叶子……”,最后蒋关上大铁门,走出去的背影(镜头再长点更佳)。老白玉兰树的四次出现,都与人物的境遇、心情相连,正可由此深邃起内涵。景语皆情语,去生硬,感真情,水乳更可得交融。
访谈后记
希望以上呈现给读者的,是一个真实梁子的个性和述说,是一个能引发纪录片人对既定规则的思索,是一截纪录片实践中有探索价值的现象,是生活本身的存在与发现眼睛的慧悟之融合(既指片子本身,又直片子所给予)生活也好艺术也罢,世相岂有完美,但求有玩味、有动感、有触发、有理想的追求,有现实的洞察,有拳拳之诚和赤子之心。
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博士生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
——2009-04-20 12:19:42,4444上传
影片图集 . . . . . . (更多/我要上传)
相关视频 . . . . . . (更多/我要分享)
对本影片资料作出贡献的会员 . . . . . .
4444(创建者)